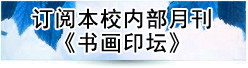自古以来,草书创作相对于篆隶等书体来说,数量极少。草书从旭素算起,宋有黄山谷,明有徐渭、祝枝山、王铎和傅山,清代崇尚碑学,其间仅蒲华一人。民国时期书家大多是行楷书面目,像鲁迅、郭沫若这样成就突出的书家也不例外,直至当代,有毛泽东、于右任和林散之三位,各有千秋。毛泽东晚年草书不再是单纯的旭素,以古人神采,浇心中块垒。于右任前半生写魏碑,使渐趋颓废的碑学再起波澜,后半生致力于“标准草书”,虽然消解了美的对立要素,使创作手法单一化,仍不失为一家风范。林散之强化文人清淡简约的意境之美,结合山水画用墨法,变化生姿,自成一家。散翁之后,草书创作渐趋低迷,与前贤不能相颉颃,但不乏一些代表性的草书家,如沈鹏、聂成文、马世晓和王冬龄等,笔者再有意识地附上近期专业报刊极力推出的唐双宁,对当今草书创作略加综合评述,作一些必要的反思。 沈鹏先生在草书创作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,立足点是对线条的认识和塑造以及对书法个性的强调: “在书法的表现要素中,我看重线条。线最单纯,也最丰富。唯其单纯,所以其丰富性更可贵,也更难得。丰富不是‘驳杂’。单纯不是‘直过’。单纯包孕万物,丰富趋向一体。¨¨¨比之结体,线是更基本、更内含、更活跃的因素。¨¨¨书法作品的总体协调与精微把握,都依赖连续与断续的、一气呵成与多种形态的、有形与无形的线条贯穿其中。” “古代大家的作品,个性特征是鲜明的,有创造性的。学习古代大家之所以得其外形易而得其神韵难,其中线条是由外形到神韵的最重要的手段、桥梁,更确切说是基因。¨¨¨传统与创造是统一体中的一对矛盾,没有人能够绝对摆脱矛盾的任何一方。有才能的艺术家善于把握从传统到创造的转化,从当代生活与艺术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坐标,形成独特的风格。” 沈鹏独具慧眼,选择画名掩盖书名的蒲华作为取法对象。蒲华从黄山谷中出,线条有别于旭素的一味狂放,静中有动,更显深沉。沈鹏在线条方面的经营通过以隶作草来实现,但沈鹏纯粹的隶书罕见,也见不到纯粹的楷书作品,所创作的大多是介于隶楷之间的碑体,但很难说依据某一家,大多似楷非楷,似隶非隶,说古不古,说今不今。他的很多题字和展标有同样的通病。转折处弃方求圆,失之圆滑,在草书创作中使用同样的使转方法,手法单一,线条有时运笔涩滞,不够凝练,显得僵硬,墨法缺少变化,结字荒率,有松散之弊。总体上看,沈鹏书法胎息蒲华,没有脱去形貌,无法超越蒲华的艺术境界。蒲华草书并不刻意于碑形而重视稚拙的质朴的自然之真,表现更多的是“趣味”,暗示了他个人对书法形式的理解,行笔飞动,奇肆跌宕,点画俯仰流而不滑,形成真力弥漫、气势回环的线条。章法出奇制胜、纵横开捭、跌宕潇洒,脱尽尘俗,另开畦畛。沈鹏学蒲华而未能自立门户,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 对马世晓草书,评论反差极大,先看两位名家的评论: “看到马世晓先生的作品我颇受启发。他作品所表现的东西,是我想去完善的,并唤起了我的创造意识,因此看后我很激动。” 沈鹏 “马书清奇绵劲,如当风杨柳,柔中寓刚。更施机锋变化,神鬼莫测其踪。”刘正成 而贬之者则认为其用笔尚未得法,过于苛刻,作为在当世有一定影响的草书名家,马世晓在创作中有自身的立足点,对文词选择和幅式安排各尽所宜,线条经营和墨色变化更是其用心良苦所在,线条追求绵里藏针和柔中有刚的感觉,局部看起来很扎实,然而从整体上来观摩欣赏,不难发现单调和雷同,自开笔至终篇有太多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缠绕,结构摇摆,极尽跌宕但没有复归平正。有人形容马世晓草书“像流动的诗,飘游的云,奔泻的水”,不难发现,这些都是形容运动的字眼,而没有静态描述。线条缠绕不清主要源于笔法的单调和汉字结体丰富变化的无度消解。虽然草书已经符号化,但无论如何夸张,仍有形体要求。马世晓想通过线条牵丝连绵营造出整体气势,问题是一泻千里的势流有了,因为正书基本功不扎实,就显得飘飘荡荡。并且多年来书风一成不变,最终只能是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。马世晓草书实际上从张瑞图出,将方折变成圆转,因过多雷同,更显软弱。明朱履贞《学书捷要》说:“草书之法,笔要方,字要圆。夫草书简而逸,简全在转折分明,方圆得势,令人一见便知,最忌扛肩阔脚,体势疏解;尤忌连绵游丝,点画不分。” 聂成文近年来一改温文尔雅的姿态,倡言高蹈徜徉、遨游驰骋作草书,目前有一整套塑造线条形态笔法,以碑意入行草,点画纷披,任情恣性而不计工拙,充分发挥破锋、散锋和挫锋功效,形成点线粗细、块面大小和墨色浓枯焦润等多重变化,求大效果、大宣泄和大节奏,但少细腻的一面,实际上是粗糙而不是粗犷。吴昌硕说:“奔放处不要离开法度,精微处要照顾到气魄。”学徐渭和祝枝山,点画狼藉可取,但最忌过碎,对整体气势破坏很多,尤其是渴笔应用,略显浮躁,纸面上像撒满米粒,有光怪陆离之感。“碎”是聂成文草书最大的不足所在。书家强调自我意识无可非议,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理性规范,完全真空的状态不存在。在整个心理过程中,无意识比有意识更重要。无意识是本能冲动,不能被感知时,仅是一种能量,没有附着在有意识所理解和使用的语言上,就不是明确的高级情感,虽然可以支配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,对书法创作影响很大,但与一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个人生活经验积累分不开。无意识表现,如果追溯下去,会有深刻的、看不见的实践和意识根源。“无意于佳”并不是不要“佳”,一味强调“放开写”而反对“做”实际上反落入俗套,有时用笔连带过于牵强,结字呈现俗意,作品优劣悬殊,书法内在精神表面化。 王冬龄草书受业于林散翁。作为林老亲炙的弟子,草书创作方面的成就自然不在话下,一直秉承如他自己所说的“力求在传统的汲取与发挥上有所开拓,在探索新意时不忽略东方艺术的固有精神”,字里行间多了股遒美娟秀的文人书卷气息。他目前的草书形式与自身的创作观大有关联: “草书创作的最高境界,我以为应当是手心相忘、物我俱化,个人精神天地与自然宇宙融会为一。其点画线条‘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’,畅其神、抒其情、写其意。 ¨¨¨中国书法是东方文化传统的象征,但又是最具有表现性艺术形式。当前东西方文化撞击与交流,必然促使书法艺术有新的开拓。人与社会已经充满了‘现代意识’,难道书法艺术还能无动于衷吗?” 王冬龄草书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显得很“油”,信笔过多,存在过多的缠绕和勉强的牵丝。周星莲说:“凡作书,不可信笔,重思尝言之。盖以信笔则中无主宰,波画易偃故也。”根本原因在于是以草论草,一味强调形式至上,近年来他对“现代派”书法的追慕极大地影响了自身草书创作格调,形式高于内容。笔者近期所见他的作品集中,很多对大量古碑帖的临摹都是为了寻求单纯形式变更,并非出于扎实技巧锤炼的目的,失去古法支撑,只能剩下空洞的形式,下笔油滑单调也就不足为怪,古人说“真书难于飘扬,草书难于凝重”。草书应熟而求生,行笔得意处宜留。因行笔迅疾而控笔少,速度太快,许多书写中本身应具有的顿挫、聚散和开合等节奏变化隐匿不见,结字过于振荡,作品形式雷同,运笔中将林散翁的绞锋捻管方法过于强化而成痼疾。所以,目前王冬龄草书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是习气而并非风格。 针对唐双宁的草书必须申明,并非是出于某种创作方面成就进行评论,而在于他的创作导向代表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心态和模式可用“燥”字来概括。在这之前,一些专业强势媒体有刻意拔高之嫌,其中不乏某些名家作秀:
“双宁先生对草书情有独钟¨¨¨心灵手巧,古今贯通,运用自如,习之既久,自己的素养和个性逐渐渗透在字里行间,正是步入了随心所欲的境界,已然具有自我的书风,笔走龙蛇,为之喜出望外。¨¨¨双宁先生的书法,若长枪大戟,屈铁盘丝,豪放不羁,气度恢弘,于无法中而有法¨¨¨具有自己的个性,有其独到之处,故为观者所称道,也就是千百年来,真正书法家之所以一直为大家所仰慕,它的核心问题,就在于斯。” 实际上技法尚未过关。草书创作需要高超的技巧,不能埋汰技巧、忽略技巧,更不能将随意发挥当成超越技巧。任笔为体、狂荡失法,这是目前很多草书创作者的通病所在。潘伯鹰在《中国书法简论》中说:“以草书的艺术和技术论,草书是最高境界。因之,学书者不能以草书服人,终不能为最卓绝的书家。”对于这样偏激的认识必须进行纠正,不能认为草书高于其他书体,以草书成就来衡量书家的历史地位。实际上,无论任何书体要想有所建树都很难,都应该值得肯定。米芾以行书名世,林散之以草书名世,并不能认为林散之在书史中的地位就高于米芾。单纯以草书成就论成败得失,所兴起的“龙飞凤舞”病态创作使得书法正常发展步履艰难,一些虚张声势、招摇过市而又附庸风雅者跃跃欲试,认为草书可以立马奏效、信手而作。片面而固执地一味求狂,导致当今书坛既无值得玩味的草书,更少有人坐冷板凳研习楷、篆、隶等正体。如今展览,正书数量处于劣势,行草书占有绝对优势,但细究起来出类拔萃者并不多,尤其是狂草更是难觅踪影。某些动辄笔走龙蛇的草书家和口若悬河、妄下雌黄,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空头评论家,以讹传讹而误导人。 草书最初产生是因字体简化要求,出于实用便捷的目的,使结构简约,字形更加抽象,书写自由度增大,艺术表现性也随之益加丰富。寻根究底,“草”的正确含义是指汉字简写,而绝不是胡乱潦草意思。点画狂驰、笔势振荡、鸦栖蛇窜、任笔为体和聚墨成形皆为草书病笔。草书对墨色、点线笔势以及结字篇局安排难于其他书体,仍具有法度要求,只不过与正书相比,是不可视的,是超越常规的。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中说:“作草书难于作真书;作颠、素草书难于作二王草书,愈无蹊径可着手处也。”学草书应先在篆、隶、楷三种书体中各选一二以固基础。大师正是如此,张旭、王铎以楷作草,怀素以篆作草,于右任以碑作草,林散之则以隶作草。草书创作要善于把握创作的契机和表露情感的意绪,既是技巧也是才气,既有灵性也有胆识,既是线条也是心音,脱离固定程式化模式,完全按照书家的情感的节律随心而生,绝无一定的格式和成法。 综合来看,一方面,在压抑甚多的现代社会,如果以草书来抒发自身情感,不失为最佳方式之一;另一方面,日益浮躁和忙乱的社会环境使得对于技巧锤炼失之荒芜,这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。在很多草书创作者中,包括上述名家在内,他们的通病就是面目雷同,表现形式单一,毕竟,草书还需要过人的才情,不仅仅是功力技巧的积累,也就是说,并不是人人都适合,都能写草书。历代书家无不视草书为畏途,真正能够进入大家宗师行列的寥若晨星,只有很少功力和性情俱佳的书家能够到达理想彼岸。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中说:“书家无篆圣,隶圣,而有草圣。盖草之道千变万化,执技寻逐,失之愈定,非神明之得,孰能止于至善耶?”虽然杰出草书大家成功的立足点不同,但必须有独特而超前人的创造。历史中的狂草大师,是永恒的风景,是一座丰碑。对于热爱狂草的书人来说,呼唤草书大师,期待新的草书大师的出现,禁不住要潸然长叹:今人谁解草书真味?